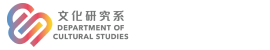在「後垃圾徵費」時期 回收何以成就文化?
作者:梁仕池教授
出版:2024-06-04
轉載自:明報新聞網
過去半個世紀,面對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增加的廢物量,各地政府在不同時段提出的方法、手段,最後殊途同歸地成為今日為人熟悉的「3R」運動——減少(reduce)、重用(reuse)、回收(recycle)。3R的出現,不僅將倒垃圾這一日常行為牽涉到全球垃圾危機,而在探討處理廢物之法的過程,也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身分、反思既有的生活方式,及釐清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,在地球與各種相生相依的物種平等共存。
讓垃圾回到我們的日常視野
香港環境當局於2013年已經推出「減廢藍圖」,教育公眾「咪做大嘥鬼」,提升公眾對環境保護的責任感。然而,多年來垃圾棄置量仍居高不下,堆填區已飽和到難以擴建的地步。垃圾似乎仍然只是個逐出家門之後,便眼不見為淨的「暫居體/佔據體」。
直到2024年,垃圾徵費條例開始宣傳到宣布暫緩實施的這5個多月,香港社會才對垃圾出現前所未有的關注。雖然引起各式社會焦慮與爭論,垃圾徵費所引起的社會作用(social effect),還是相當顯著的——不少人開始計量每日棄掉多少垃圾、苦惱如何在家分類、問訪哪裏有回收設施。很多人說,現在不單生孩子,連倒垃圾都要「考牌」。
推動落實條例的嘗試,確實動搖了我們「眼不見為乾淨」的處理垃圾習慣。這種習慣從前不受打擾,大抵是由一個「多棄置、重衛生、弱回收」的廢物管理系統所支撐。這個系統已然不勝負荷,人人都需要回應垃圾危機。如今,垃圾徵費暫緩推行,必然會令社會對於垃圾的關注大減;但香港700多萬人與我們的垃圾故事並未翻篇,這個挑戰仍在。而這個減廢挑戰,只會因為我們從準備期(垃圾徵費作為協助)直接跳到實踐期(無垃圾徵費的框架支撐)而變得更加嚴峻。
「回收文化」的背後
本文旨在回應政府提出的「回收文化」一詞,認為不應將其簡化為垃圾收費、減廢回收的認識或認同這類空泛的虛詞;這個「回收文化」背後,是更實質、更有效的行動網絡。
國際社會關注的可持續垃圾管理,已成為氣候行動對應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課題。例如,本港環境當局2013年推出的《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-2022》,提及倒金字塔式的「廢物管理架構」。它強調五部曲,最頂(即最優先)是源頭減廢,然後分別是物盡其用、分類回收、循環經濟,最底層是堆填和焚化,亦即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最不可取之法——不止浪費資金,更加劇溫室氣體排放。可見,轉廢為寶、資源循環已經成為在地廢物管理和環境治理的新情勢。
同時,新興的綠色或循環經濟,也使學界關注到垃圾成為被忽視的公共資源(commons);要達到共管共享,不單要提升收集、轉化和分配效率,還要考量文化認同、生態公義和政治協商等問題之間的拉扯。也許技術與法規大同小異,但以上問題所構成的「民情」,卻因地而異。也因此,減廢運動通常以城市為單位。城市所提供的配套和法規,才是影響到人們有多投入和建構「回收文化」的骨幹。
美國社會學家Lily Pollans在Resisting Garbage(2021年)一書比較西雅圖與波士頓的案例,提出「弱回收垃圾體制」(weak recycling waste regime)理論:重點在於不應只考慮如何令市民被動地配合規例,而是呈現垃圾問題的過程能讓那些涉眾參與其中。這理論更認為,一個回收垃圾體制的形成,考驗慣性依賴由專家知識所建構的管理制度(technocracy),在與環境和垃圾相關的公共規劃及政策制訂過程中,能否採納或包含非官方的減廢經驗,亦即民間智慧(local knowledge)或公民科學(citizen science)。
民間實踐經驗 可補官僚知識缺陷
本港垃圾徵費政策被批評講解不足和欠缺配套等問題而兩度延後,政府實行8個星期的「先行先試」,以了解不同民眾使用「綠色徵費袋」所面對的難處,並以問卷收集他們意見及對徵費計劃支持與否,為試行計劃畫下句點。當局於5月底向立法會提交的試行計劃報告中,強調絕大部分參與的市民不認同徵費計劃。報告裏羅列的眾多批評,例如「擾民」、「勞民傷財」、「難以監控違規」等,似乎成為政府「順應民意」暫緩計劃的主因。
試行計劃讓官方作出一個「有根據、比較科學」的政治決定;而持份者的參與,則淪為表態的作用。此等技術官僚所產出的知識盲點,難免顯得決策者「離地」,亦不符合「走入群眾」的調研精神。
民間對於環境議題的看重,促成了許多實踐;累積下來的經驗,提供了思考垃圾(徵費)這個難解問題的方向。例如早前電視節目《新聞透視》已提到,環保署曾與不同團體合作,所推行的社區垃圾回收試驗計劃,涵蓋各種住宅類型可使用的不同清理垃圾模式。
可惜這些寶貴經驗,在當局制訂「綠色徵費袋」使用指引時並未被列入參考,使局方代表在宣傳期間收到屋苑持份者提出不斷湧現的執行困難時,才如夢初醒。
另有組織在4月舉行「『零』垃圾的想像——基層勞工與垃圾徵費大辯論」,清潔員工會代表認為,政府應提前接觸廢物管理最前線的單位和群體,諮詢前線清潔員的難處(例如處理違規垃圾),並請教有何應對方法。亦有環團、居民組織和研究單位聯合推出民間「先行先試」的「垃圾審計」,運用社會設計的方法,蒐集劏房住戶減廢的痛點,及跟參與者商討可行方案;住戶也提出多項建議,例如設立廚餘通道、流動回收點、天台回收等,有助回收高達87%家居垃圾。還有回收業者建議參考鄰近同樣高密度的城市,例如首爾和台北,提出落實垃圾收費的策略大可不必一刀切,宜考慮分階段、分區、分範疇的漸進式推行,方能有效紓緩推行垃圾徵費所引起的社會陣痛。
以上種種充滿民間智慧的經驗和實踐(局長或稱為「坊間資訊和意見」),如果受到重視,理應能夠修補技術官僚的知識缺陷,使香港日後所建立的回收垃圾體制,能夠培養出強韌、具彈性的回收文化。
從「responsibility」到「response-ability」
我們未曾有垃圾徵費,就已經進入「後垃圾徵費」時期(假設落實遙遙無期)。我們對於垃圾回收文化,或許能夠有一個更複雜、有效、跨界別的理解。一個強健的回收垃圾體制,不應只停留在對垃圾收費之認識、認同的框框裏。在這個回收文化中,決策者也不止着重宣傳教育減廢回收的重要性,以提升市民的道德負責(responsibility),而是培養所有人對垃圾問題的「回應力」(response-ability)。此一文化不需要大家被動地等待完整的配套與規則出現,而是鼓勵大家探索在(仍不完整的)框架以外的減廢經驗和實踐,產出更多能夠讓彼此分享的就地取材、因地制宜的應對知識和技能,以創意且務實的方式,提升與香港社會共成長的回收垃圾體制。
原文網址: 在「後垃圾徵費」時期 回收何以成就文化?
查看相關研究項目的詳情,請點擊這裏。